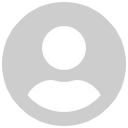师父:不坐?好,掌声鼓励一下。
蔡老菩萨:我也不太会说话,有些说话的地方可能大家有点不太懂。我在西安快蹲了60年了,我是从上海支援大西北,本身是扬州人,所以说话呀,有点四不像,方言的话有点不太同,不太妥当,我尽量要叫大家听懂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1956年支援大西北,到大西安是一个纺织工人,进纺织厂三十多年。因为这一生全身的病,因为旧社会家里比较苦,成天干活比较多,所以到了纺织厂从来不嫌苦,也不歇病假,所以的话得了很多病。到了退休了,不久,我已经不行了。
第一件病,就是乳房上出了一个大问题。早晨出去大家都在门口练功,那时候你们河南有一个香功,到了我们西安,大家都在那里练香功。练了半个月,我这个右侧这个乳房上,长了一个疙瘩,跟核桃一样大,硬得很,硬得不得了,像这样。我也没办法,我说这怎么办呢?就到我们厂医院检查.检查了以后,他说可能是癌症,可把我浑身吓得发软。就转到我们那里纺织工人的职工医院,检查还说是癌症。我不相信,你们都胡说呢。我又到军大,就是第四军医大学医院,他说确实是癌症。哎呀!这时候我就到南郊一个肿瘤医院,是中国和日本合资的,这个医院世界上都有名气的。到那里一检查,他说你是乳腺癌,你不赶快挖掉,你就要扩散全身。哎呀,我这时候就想到,这怎么办?就和孩子们商量,做手术吧。这一场手术,姐妹们,想起来我真是伤心啊!这个奶挖掉了,把我这半个身子的肌肉全都挖掉了,除了皮(保留)。还要接受了化疗、放疗,一共花了56天,我还记得。有人送到那个激光里头,两分钟就出来。进去的时候是我自己走去的,出来的时候,我那个大儿子挨着到我,都在那里守到,还有老头子,都把我抬出来。那个滋味呀,真不是人过的。
放疗了56天,后来回去以后,红血球、白血球一起杀,我所有身上的这些病都来了,我简直是活不成了。我吐血呀,我吐了十八年的血呀!有时间大口大口吐啊!在四年以前,我们家孩子下岗了,大孩子在上海打工,孩子们有的去上班。我吐那个血,那个脸盆,一脸盆的血往下吐。那一天我实在是难受,我的孙女在上学,我说奶奶今天很难过,她说我三点钟放学,她刚过去在那儿挂吊针,守到外边,那个血“哗”,像自来水一样的往外吐。我的孙女儿看到了就喊,“大夫,救命哦!救我奶奶哦!”,抬上去就抢救了五天五夜。
这时候我就想,哎呀,这里没命啦。后来我就慢慢自己想,“活下去,一定要活下去”,就是活下去。就住院,也是接着住院,大夫都说,你活不了多久啦。我活不了多久也要活。回来想想,哎呀,真活不了成啦,就想上吊。一想,我平常也念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,光在念佛,那时候不知道有般舟,般舟步都不懂,就在那儿念念念。我心脏病,先天性的房颤性的心脏病,也犯啦。那个心脏一天到晚,抵抗力没有了嘛,“叮咚、叮咚”,我就跟偷了人家几百万一样,“叮咚、叮咚”。我纺织厂吃饭快,胆囊炎也变成胆结石啦,胆又痛,胃又疼,腰椎盘下掉,坐骨大神经(疼),这个纺织厂走路多嘛,疼的。后来我这个大骨头糜烂,全部都来啦。我可怜的,哎呀!真是没有办法,没有我活了。还有这个地方颈椎病,小脑萎缩,全都有啦。
我说,我今年,那时候已经二十年前了嘛。哎呀,我的脑子就想啊,都不知道,我就——哎呀,这怎么办呢?今天心脏太激动了,回想起心酸的时候,我怎么过来的,我就想起来这些酸心的事情啊,我都说不下去啦。我今天能站到这个地方啊,和我们这些菩萨们汇报我自己,我这个千言万语,我实在是说不出来的(激动)。所以在这么多的病的情况下,我怎么会到了般舟来的呢?我躺在家里不能动啦,爬不起来了。
师父:老太太方言啊,“拜舟”就是般舟啊,“拜舟”,就是般舟,踏般舟。
蔡老菩萨:我们这个扬州人说话,就是这个吐字音有点变。我的女儿她到了般舟,到师父这里来工作了。女儿给我打电话回去,叫哥哥从上海回来伺候你,师父打电话给我女儿,女儿给我打电话。她说,妈妈,你到我这里来,这个地方,我们的师父,这个般舟怎么怎么好。我说,“我也不知道,我这个样子能走吗?”“我给你把飞机票买好啦。”“哎哟,妈妈还能坐飞机呀?哎哟,妈妈都要交粮本喽。”我们这个西安人呐,活不成了才叫“交粮本”的嘛。“哎哟,妈妈不行啦。”后来,到了下午又打了电话,“妈妈,给你把火车票买好啦,后天一大早。”结果没办法,我就带了全身的衣服,我大儿子送我,小儿子请了半天的假,送我到火车站,到火车站就把我送上火车。我一路上,在火车上,到达宝峰寺。到了宝峰寺,就坐那个汽车,高速公路上都坐了六个小时,不知道通哪里,我也不知道。
到了宝峰寺,我快不行了。“啊,啊,啊”,就这嘴巴光在那儿张了,“啊,啊,啊”。我住在窑洞里头,几个男菩萨,我坐到轮椅上,把我抬到窑洞里头。我就躺到那里,“哎呀,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,念不清。结果我到了第二天,外边有人喊:“你们快出来,西方三圣在天上!”我一下子从床上想站起来,站不起来啦,站起来“扑通”往地上一跪。唉呀,怎么办?我就爬,爬到那个门跟前看,看天。哎呀!西方三圣在前头,(西方)三圣走过去,那个后边五色的彩霞,哎呀,漂亮得很!把我看得高兴的。哎呀!这个地方真有神通!哎哟,听到那个大殿里头,那个声音,不是念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,我也在那里,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。我又爬进去,在床上,“哎呀,阿弥陀佛,阿,阿”,舌头硬啦,都念不起来啦,我就这么念。念了以后的话,第三天就下去,下来呢,也是人家把我抬下去,抬到那个大殿门口。坐到轮椅上,推了两天,我跟我儿子说,“不行,不行。这都像托儿所的娃娃一样了,这推的,我能念好佛吧?”我走到轮椅下,轮椅撂到院子里去了,不要了,祸害。我儿子出家了,搀到我,我就拿着拐棍,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。念不清,走得也不对,我知道,不管它,尽管念,尽管念,啥都不要想,就念。
念到两个礼拜了,我儿子,就是大寮上没人做饭,几百人吃饭,就给我说。我说,你们走吧,你妹妹要领众,都很忙,不要守着我,我不要紧。我说,我要是往生了,这里这么多的师父,这么多的菩萨送我往生,我请还请不到呢。不管它,往生也是好的。我说,不往生了,我一定要好好念佛,要好好走般舟,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,就在(那里)蹦、念。儿子他们统统各人有各人的任务,我一个人在那个窑洞里头,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。要想起来尿都起不来,哎呀,都尿裤子啦,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,就那么爬呀、爬呀。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去念,儿子他们忙,到了晚上了在大殿念佛,师父们都在那儿念佛,菩萨都在那儿念,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。我拿着拐棍也是慢慢的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。可不知道,哪一位师父,就念。从太原来的一个姑娘,漂亮的姑娘就跟我说:“老菩萨,放下拐棍”,“哎呀,不行。”“来,唱,阿弥陀佛,北京的金山上”,我说这样,“阿弥陀佛就是那金色的太阳——”,转了几个圈,把我的拐棍转丢了。我就围着这个大殿,就在转过来转过去。呀,我的拐棍呢?没有啦,拐棍没有啦。没有啦,不要啦。我就那样子,半个月的时间,丢掉了我的轮椅,又丢掉了我的拐棍。我就围着大殿,就走,就是这样子,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。眼睛一闭,有时间,半夜里睡不着了起来,就在那个窑洞里,抓住那个床头,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,我啥也不想啦,什么都忘掉啦,放下啦,就念。
念半个月以后,哎呀,菩萨们,我的业障来啦。要谈这个业障,坐骨大神经疼,疼得就跟那个螺丝刀在里头搅一样的痛。这边疼上一个礼拜,又到这边来疼上一个礼拜。腰又疼得哟,走得,哎哟,疼得……。好,这个大骨头,这个地方腐烂,已经在厂里头都看了,他说你已经终身瘫痪了,你不得好了,因为这里头有水了,要叫我抽水,拿这么长的管子。哎呀,我不抽不抽,不能抽。这一抽,我彻底完蛋啦,不抽。我就走这个般舟,坐骨大神经也走好啦,我这个地方也不疼痛了。你看我,跟你们再走,我现在八十了,今年,七十八到的宝峰寺师父那里,我跟你们走多远,我腿不疼。走的时候为什么给我拿个拐棍?她们说,晚上的时候上个台台给你拄个手,要不要这东西干啥嘛?拖累。所以说,我不疼了嘛,我现在腿不疼了嘛,我再也不疼了嘛,我啥都好了嘛!你想这个般舟力量大不大?啊?你看就这么,我瘫痪的,坐了轮椅到达宝峰寺的。
后来我这个肺上痛。,告诉大家,这个酸甜苦辣,根本就不得好的。大夫都说了,这个叫什么?肺,你这个乳房手术做完以后,那大夫给我说,还有像火柴棒半个那么大的找不见了,一定要放疗、化疗。可是我在这个化疗当中,那个刚进来的那个先进设备搭起网子,摆在这个地方烧。哎呀,烧得我呀晚上,那个皮呀肉呀往下掉哦,就像那个红烧肉烧糊了一样。自己想想伤心那!我咋这么大的业障啊?我前世里今世里做了什么坏事啊?自己就在想啊,我说,我对爸爸妈妈可孝顺啦。小时候(跟)日本打仗,这些事都不给你们讲了,小时候经过了多少苦难;我公公婆婆没有工作,那时姑娘小叔子都多,我每个月纺织厂工资都高,一发工资,这也寄,那也寄。我没有做过坏事啊,我怎么这么大的业障啊?我咋这么大的业障啊?疼得我死去活来的。医生化疗了,放疗了56天。这56天以后,都回家了。我老头子就给小孩讲,你妈那个病不得好啦,算啦,放弃吧。可是我这孩子好得不得了,我这个大儿子为了我出家了,对我从来不说一句烦人的话。姑娘,无微不至地关怀。小儿子是个马大哈,他也不坏。哎呀,我可怜的,吐血呀,难过呀,站不起来呀,都是他们。“爸爸年经大啦,你别计较他啊,有我们呢。”我们这个孩子好的不得了,哎呀,我说我也是前世修的。
所以说,这么多年,等到就是前年吧,我女儿到师父这里。师父这里的话,行法就是领众,打电话叫我,我都来了,来到这个地方,就跟着行法。哎呀,行得呀,实在是不行。好像呀,开始这个行,这个腿疼,腰疼,疼得是没有办法。我住的那个房子是在窑洞里上头,上那个台台,要有二层楼高,上去,人家要拉我,“不拉”,我摔得那个腿上哦,青一块、紫一块,腿肿得呀,裤子都拽不下去,脱不下来。不管它,吓退不倒,往上去,我说我吃些苦不害怕,吃这个苦。走,走上去,坐两小时,跑到那个窑洞里头,喝点水,弄点馍一吃。又下去,走,跟到师父在那里走。
走了三个月以后,师父说的,出去弘法,走不走?走!第一站就到了徐州,就那么走,走。我那个疼痛,那个螺丝刀搅得,后来我不是这个腿疼嘛,疼得没办法走般舟。哎呀,这么疼啊?哎呀,太疼了!“好啦,好啦”我自己跟自己说话,“好啦,好啦,世界上的老人,你们都不要疼啦,给我一个人疼吧。” 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”,就那么蹦了将近一个多月,在窑洞里头那个架子床,吊着那个架子床,“咚、咚”,“阿弥陀佛,都不要痛,给我一个人痛。”你不知道那个疼得死去活来的呀,那个汗水,我在孩子面前没掉一滴眼泪,给大家我都不说,这是我自己的业障,疼啊!到了徐州,我不疼啦!跟了师父弘法。前年吧,弘了五个省、十三个道场,我跟着跑得可快啦,我什么也不要啦。想到我们这个师父走般舟,哎呀,我有时间回去看看,因为我们那个小儿子,有点不争气,一回去看看,要不了几天我就想到师父了。哎呀,师父那个佛号一叫,我都睡不着觉了,给老大说,赶快赶快,把东西收拾收拾,赶快赶快要去找师父。不行不行,心不安。师父,师父在半夜里都在叫我呢,“演子,阿弥陀佛。”。我也“阿弥陀佛”。
现在我提起这个阿弥陀佛,我这一次过年又回去看了一看,阿弥陀佛,在我的周围,我只要静下来,我的周围全是阿弥陀佛。那天到了火车站,人家说话听不见,“阿弥陀佛”,我(听到)全都是阿弥陀佛。庙里来少一点,到外头,公共场所,包括坐火车,火车到头,我都念“阿弥陀佛”,全都是阿弥陀佛,大脑里就是灌的阿弥陀佛,什么都没有。我变成瓜瓜子了,我给儿子讲,妈妈瓜了。瓜了才好,瓜了才好。所以说,我的心中就是个阿弥陀佛,什么都没有。
暂无附件